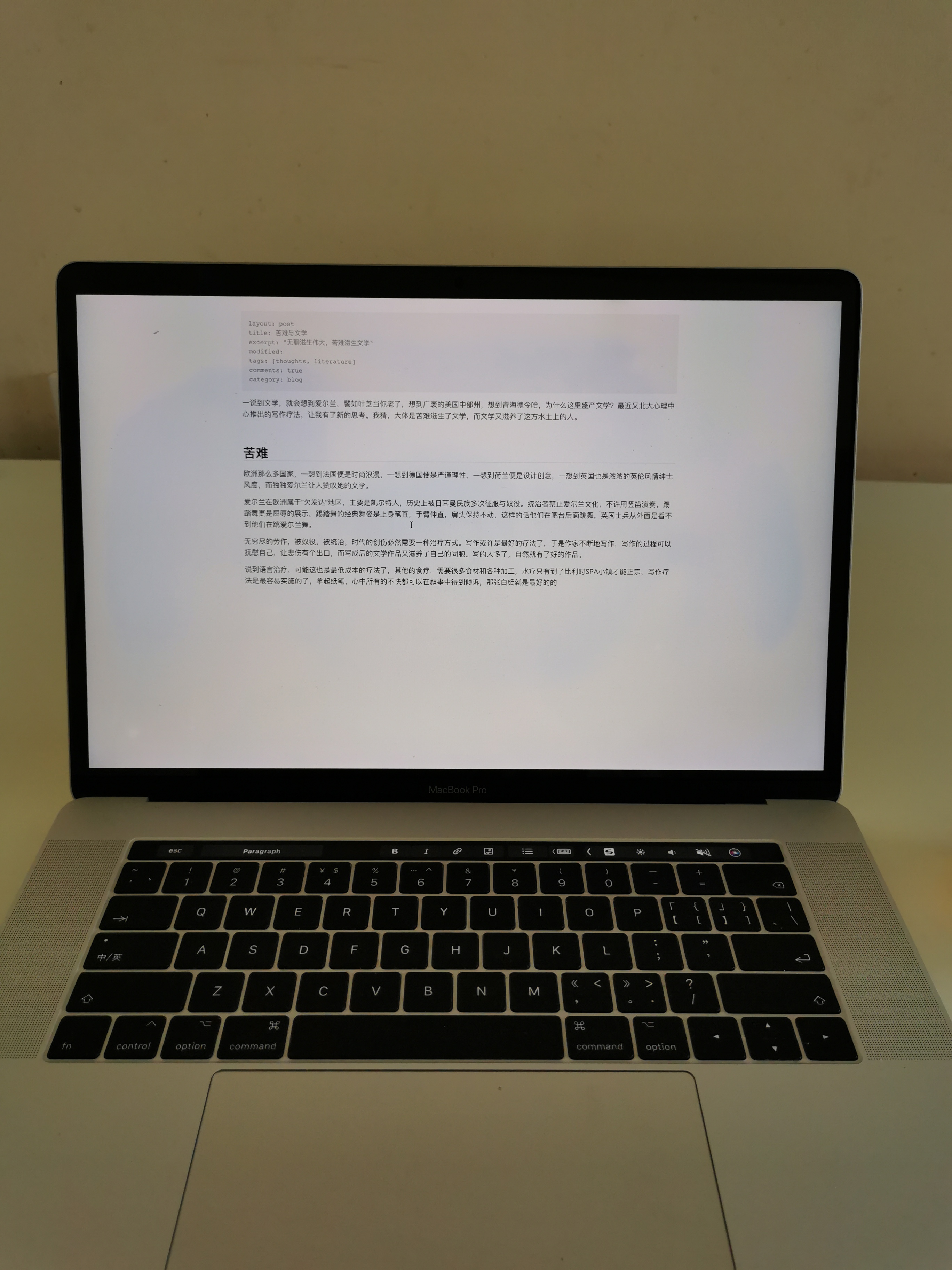一说到文学,就会想到爱尔兰,譬如叶芝当你老了,想到广袤的美国中部州,想到青海德令哈,为什么这里盛产文学?最近看到北大心理中心推出的写作疗法,让我有了新的思考。我猜,大体是苦难滋生了文学,而文学又滋养了这方水土上的人。
苦难
欧洲那么多国家,一想到法国便是时尚浪漫,一想到德国便是严谨理性,一想到荷兰便是设计创意,一想到英国也是浓浓的英伦风情绅士风度,而独独爱尔兰让人赞叹她的文学。
爱尔兰在欧洲属于“欠发达”地区,主要是凯尔特人,历史上被日耳曼民族多次征服与奴役。统治者曾禁止爱尔兰文化,不许用笛演奏。踢踏舞更是屈辱的展示,踢踏舞的经典舞姿是上身笔直,手臂伸直,肩头保持不动,这样的话他们在吧台后面跳舞,英国士兵从外面是看不到他们在跳爱尔兰舞的。
无尽的劳作,被奴役,被统治,时代的创伤必然需要一种治疗方式。写作或许是最好的疗法了,于是作家不断地写作,写作的过程可以抚慰自己,让悲伤有个出口,而写成后的文学作品又滋养了自己的同胞。写的人多了,自然就有了好的作品。
文字的治愈
说到语言治疗,可能这也是最低成本的疗法了,其他的食疗,需要很多食材和加工,水疗只有到了比利时SPA小镇才能正宗,写作疗法是最容易实施的了,拿起纸笔,心中所有的不快都可以在写作中得以倾诉,那张白纸就是最好的听众,她安安静静地聆听,与你相伴,纸笔摩擦的沙沙声,便是对你的最好回应。这大体也是所有心理治疗的基本方法了,倾诉与聆听。
使用键盘写作,又有新的感受,键盘的咔咔声,想法从大脑涌出,化作指尖的舞蹈,这些舞蹈又幻化为屏幕上整整齐齐的文字,而如果这个文字再会有人阅读,与你遥相呼应,那便是神交,也是现代人独有的治愈了。
幸福的人,大体是没有时间创作的,尤其是非实用写作,恋爱中的情侣幸福了,甜甜蜜蜜、卿卿我我,或联手做饭,或者携手出游大体是没有时间写作的。只有分手了,吵架了,异地了,情感没有一个去处,才会有通过文字来疏解的冲动。
大师辈减
《在昌平的孤独》,海子
孤独是一只鱼筐/是鱼筐中的泉水/放在泉水中
孤独是泉水中睡着的鹿王/梦风的猎鹿人/就是那用鱼筐提水的人
八十年代,海子伤心了痛苦了,只能坐昌平345路公交去北京,来回坐反复坐,最多去小酒馆喝点酒,还能做什么呢?只能写诗了。诗是他的治愈,治愈那些求而不得的波婉、佩佩、安妮、诗芬、芦花…
这些年明显感觉文学大师少多了,想来也是人民的生活变好了,也难有什么苦难,即便有痛苦,也有很多音乐、电影、演出作为替代,或者约上三五好友胡吃海塞,或桌游密室剧本杀,唯一缺的就是人民币,有了钞能力,什么都可以治愈。
疫情期间,因为各种生活受限,也能明显感到写作的人变多了,譬如我自己,要是没有这五一的疫情,大概率我会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流浪,而不是在这里码字。
农村
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,很多的文学是来自农村。爱荷华是美国中部农业州,广袤无垠的玉米地,远离灯红酒绿的大都市,最近的芝加哥市也需要三四小时的车程,然而爱荷华大学却有全世界最好的创意写作项目。山东高密,高粱地里出了莫言。我想大抵是因为农村的社会模型更为简单,不像大城市各种包装伪装,有时很难看到社会的本质,而乡野更本真,人性的善与恶都能轻易地表露,因而作家也有更多机会去观摩这众生相和浮世绘。
我的老家素有「中国小说之乡」的美誉,兴化早期是农业大县,河网密布,历史上有写《水浒》的施耐庵,今天有毕飞宇这样的文豪,小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,到今天回想,初高中时,正是那些随处可见的不知名乡野作家的作品滋养了我,伴我度过了那漫长又百无聊赖的夏天,也构筑了我年少时的精神家园。有次漫步在布拉格,看着伏尔塔瓦河的绵绵清波慢慢流淌,捷克的俊男划着皮划艇驶向河心岛,竟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读的小说,水乡的小伙撑着船篙去接垛田上劳作的姑娘。
无聊
苦难或可催生文学,而无聊却可滋生伟大。Python的发明者,在某个圣诞假期,觉得太无聊,便创造了这个风靡全球的编程语言。确实,当今社会,要无聊实在太难了,各种消遣娱乐,轻易便能填满你的时间,要能无聊,必然是什么都经历过了,阅历颇丰才能觉得无聊,在脱离了所有的低级趣味后,人便开始追求更伟大一些的东西,一旦做成便可能惊世骇俗。
等下一篇再来展开说说无聊。
这个码字的假期